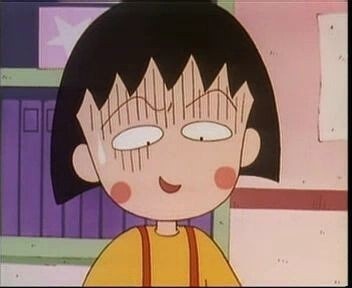《杂阿含经》“比丘相应”的内容为卷三十八第1062~1080经和本卷第1081~1083经,是和比丘众有关的经文。
上一卷的最后一经(1080)到本卷的前三经(1081、1082、1083),都可说是关于比丘托钵乞食的日常生活中可注意的事项:从托钵乞食的路上应摄持诸根(1080),行为应遵循戒律(1083),不挑选施主(1083经对应的南传经文),乃至乞食后打坐时应舍离欲心(1081、1082),都是关于比丘行走人间时该如何修行的经典。
在家居士要工作讨生活,为五斗米折腰,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乞食。对于志求解脱的在家居士而言,这些经文所传达的修行意涵也能有所帮助。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波罗㮈ⓐ国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晨朝着衣持钵,入波罗㮈[*]城乞食。时,有异比丘着衣持钵,入城乞食,于其路边,住一树下,起不善觉①,以依恶贪②。
尔时,世尊见彼比丘住一树下,以生不善觉,依恶贪嗜③,而告之曰:“比丘!比丘!莫种苦种④,而发熏ⓑ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种苦种子,自发薰ⓒ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蝇不竞集者,无有是处。”
时,彼比丘作是念:“世尊知我心之恶念。”即生恐怖,身毛皆竖。
尔时,世尊入城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入室坐禅。晡时从禅觉,至于僧中,于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见一比丘住于树下,以ⓔ生不善觉,依恶贪嗜。我时见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莫种苦种,发熏生臭,恶汁流出。若有比丘种苦种子,发熏生臭,恶汁流出,蛆[*]蝇不集,无有是处。’时,彼比丘即思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惭愧恐怖,心惊毛竖,随路而去。”
时,有异比丘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云何苦种?云何生臭?云何汁流⑤?云何蛆[*]蝇?”
佛告比丘:“忿怒烦怨⑥,名曰苦种。五欲功德,名为生臭。于六触入处⑦不摄律仪,是名汁流。谓触入处不摄已,贪、忧、诸恶不善心竞生,是名蛆[*]蝇。”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耳目不防护, 贪欲从是生,
是名为苦种, 生臭汁潜流。
诸觉观气味, 依于恶贪嗜,
聚落及空处, 若于昼若夜。
远离修梵行, 究竟于苦边,
若内心寂静, 决定谛明了⑧。
卧觉常安乐, 诸恶蛆[*]蝇灭,
正士所习近, 善说贤圣路,
了知八正道, 不还更受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㮈”,宋、元、明三本作“奈”。*
ⓑ “熏”,圣本无“熏”字。
ⓒ 大正藏无“薰”字,今依据明本补上。
ⓓ “蛆”,宋、圣二本作“疽”。*
ⓔ “以”,圣本作“坐”。
① 不善觉:不好的念头。这里“觉”是“寻”的旧译,是投向的注意力。
② 恶贪:严重的贪欲。
③ 贪嗜:即贪欲。“嗜”为喜爱、贪求。
④ 苦种:苦的种子、来源。
⑤ 汁流:此处指在乞食时,没有摄心,持守威仪。放纵不善心,好像汤汁从发臭的物品流出来。
⑥ 忿怒烦怨:愤怒烦躁。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瞋恚嫌害”,相当的南传经文作“贪婪”。
⑦ 六触入处:由“六触”进入身心的管道,常特指六触使人心意动摇、产生贪爱的过程、时空、或情境。六触是“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这里的“触”特指感官、外境、识,三者接触,是十二因缘之一。
⑧ 决定谛明了:心中确定、真实不虚地明白了知。“谛”是真实不虚的意思。
修行止观的人能发现享受五欲虽然快乐,却也时时有苦。以享受米其林五星级美食为例,想要美食的当下,这个渴望就有“求不得苦”;享受美食的当下,在色香味俱全麻痹感官的背后是“五阴炽盛苦”;享受完美食,吃完了,则是“爱别离苦”。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毕,还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①坐禅。
时,有异比丘亦复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毕,还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是比丘入昼[*]正受时,有恶不善觉起,依贪嗜心。
时,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作是念:“此比丘不善不类,于安陀林坐禅而起不善觉,心依恶贪,我当往呵责ⓑ。”作是念已,往语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疮疣耶②?”
比丘答言:“当治令愈。”
天神语比丘:“疮如铁镬③,云何可复?”
比丘答言:“正念、正知ⓒ,足能令ⓓ复。”
天神白言:“善哉,善哉,此是真贤治疮,如是治疮,究竟能愈,无有发时。”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还祇树给孤独园。入僧中,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还,至安陀林坐禅,入昼[*]正受。有一比丘亦乞食还至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觉,心依恶贪。有天神依安陀林住,语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疮疣耶?’……”如上广说,乃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治众贤。’”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士夫作疮疣, 自生于苦患,
愿求世间欲, 心依于恶贪。
以生疮疣故, 蛆[*]蝇竞来集,
爱欲ⓔ为疮疣, 蛆[*]蝇诸恶觉。
及诸ⓕ贪嗜心, 皆悉从意生,
钻凿士夫心, 以求华名利。
欲火转炽然, 妄想不善觉,
身心日夜羸, 远离寂静道。
若ⓖ内心寂静, 决定智明了,
无有斯疮疣, 见佛安隐路。
正士所游迹, 贤圣善宣说,
明智所知ⓗ道, 不复受诸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昼”,元、明、圣三本作“尽”。*
ⓑ “责”,圣本作“啧”。
ⓒ “知”,大正藏原为“智”,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知”。
ⓓ “令”,大正藏原为“分”,今依据前后文改作“令”。
ⓔ “欲”,大正藏原为“求”,今依据圣本、高丽藏二本改作“欲”。
ⓕ “诸”,圣本作“余”。
ⓖ “若”,宋、元、明、圣四本作“著”。
ⓗ “知”,圣本作“智”。*
① 安陀林:是音译,义译为寒林,因为林木多而较凉,也是弃尸的树林,而让一般人恐惧而发凉。
② 作疮疣耶:你是皮肤长了脓包吗?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何故作疮”。
③ 疮如铁镬:脓包像铁锅一样。“镬”是古代烹煮食物的大锅,读音同“获”。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汝疮如𤬪”。
比丘打坐时起了贪欲,此时在附近的天人借由和比丘的问答,引导比丘自己找出解决方法:以正念、正智,将心念拉回到修行上。
也可参考《中阿含经》卷二十五〈因品4〉第102经念经:“欲念、恚念、害念作一分;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复作一分”,教我们辨识欲念、恚念、害念的念头而舍之,留下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这样才能渐次得到初禅至四禅,进而因定发慧。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毘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时,有众多比丘晨朝着衣持钵,入毘舍离乞食。
时,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闲①法、律,当乞食时,不知先后次第。余比丘见已而告之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越ⓐ,莫重②,前后失次而行乞食,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年少比丘言:“诸上座亦复越次③,不随前后,非独我也。”如是再三,不能令止。
众多比丘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着衣持钵,入毘舍离乞食,有一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行乞食时不以次第,前后复重。诸比丘等再三谏不受,而作是言:‘诸上座亦不次第,何故呵我?’我等诸比丘三呵不受,故来白世尊。唯愿世尊为除非法,哀愍故。”
佛告诸比丘:“如空泽中有大湖水,有大龙象④而居其中,拔诸藕根,洗去泥土,然后食之。食已,身体肥悦,多力多乐,以是因缘,常喜乐住。有异种族象,形体羸小,效ⓑ彼龙象,拔其藕根,洗不能净,合泥土食。食之不消ⓒ,体不肥悦,转转羸弱,缘斯致死,或同死苦。
“如是,宿德比丘学道日久,不乐嬉戏,久修梵行,大师所叹,诸余明智修梵行者亦复加叹。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善护身口,善摄诸根,专心系念,能令彼人不信者信、信者不异,若得财利、衣被、饮食、床卧、汤药,不染、不着、不贪、不嗜、不迷、不逐,见其过患,见其出离,然复食之。食已,身心悦泽,得色得力,以是因缘,常得安乐。
“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闲法、律,依诸长老,依止聚落,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不专系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变。若得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染著贪逐,不见过患,不见出离,以嗜欲心食,不能令身悦泽,安隐快乐。缘斯食故,转向于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谓舍戒还俗,失正法、正律。同死苦者,谓犯正法、律,不识罪相,不知除罪。”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龙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异族象效ⓔ彼, 合泥而取食,
因ⓕ杂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越”,圣本作“超”。
ⓑ “效”,大正藏作“效”,今依据圣本改作“效”。
ⓒ “之不消”,圣本作“不消故”。
ⓓ “门”,圣本作“问”。
ⓔ “效”,大正藏作“效”,宋、元、明三本作“效”,今依据圣本改作“效”。
ⓕ “因”,宋、元、明三本作“同”。
① 闲:通“娴”,即熟习、通晓。
② 莫越,莫重:不要(因为对方供养的食物好而)不按次序、重复地向某一户施主乞食。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云何处处经历诸家”,相当的南传经文作“不要过度地去诸家”。
③ 越次:不按正规次序。
④ 龙象:梵文及巴利文Nāga为龙及象的合称,在这里指大象。
上一卷第1070经中有一位年轻比丘看似不合群而被告状,佛陀则告知大众其实这位年轻比丘已证得阿罗汉;本经则相反,年轻比丘不遵守挨家挨户逐一乞食的戒律(而挑选乞食的人家),被告诫后还顶嘴说也有上座比丘没有逐一乞食,佛陀则教导这位没有证量的比丘要好好守戒,可见佛陀的因材施教。
佛陀比喻健壮的大象拔起莲藕冲一冲就可吃下去,但瘦弱的象没洗干净莲藕,和著泥土一起吃容易消化不良甚至病死。相似地,已有证量的上座比丘身心清净不染,对于戒律的细节就不需要太过重视,但未证的新学比丘则必须先着重戒律,以训练身心清净不染,否则修行容易出状况。
从这几经可整理出佛陀或尊者们常见的日常作息时间表。古印度有一日八时或六时的两种时间系统,下表是依一日八时的系统所计算而得的时间,提供作参考:
| 时间 | 作息 | 加注 |
| 06:00 ~ 08:59﹝晨朝﹞ | 着衣,持钵,乞食 | 乞食后有时间则坐禅,或有弟子发问,佛陀也会开示。 |
| 09:00 ~ 11:59﹝日中﹞ | 用餐,返回住处,洗钵,衣钵放好,洗脚洗好。 | |
| 12:00 ~ 14:59﹝日中(2)﹞ | 入室坐禅,或入林坐禅 | 或有弟子发问,佛陀也会开示。 |
| 15:00 ~ 17:59﹝晡时﹞ | 结束禅坐,起坐到大众集会的地方,开示说法或解答问题。 | |
| 18:00 ~ 20:59﹝初夜﹞ | 禅坐或经行 | 经行多在户外,故经行完,“洗足入室”。 |
| 21:00 ~ 23:59﹝中夜﹞ | 就寝休息,右胁而卧。 | |
| 00:00 ~ 02:59﹝中夜后﹞ | 休息。 | 特别精进的则起床用功。 |
| 03:00 ~ 05:59﹝后夜﹞ | 禅坐或经行。 | |
乞食,要到有在家人的地方,从僧团居住的郊外通常有一段路。一路上就捧著钵,脚步稳稳地走,眼睛看着前方要走的路上,嘴巴禁语,心念安住在自己身体的动作上,或是所修的法门上。这就是第1080经的背景。
到了村落后,戒律规定要一家家依序乞食,不因贫富贵贱而挑选对象,这是第1083经的背景。
乞得食物后吃饭,心安住在吃饭的动作上,不因是否好吃而喜爱或讨厌食物。用完餐后通常会在室内或是树林中打坐,若起了贪、瞋、痴。就必须提起正念、正智,拉回当下。这是第1081经、1082经的背景。
佛陀教导僧众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的每件事情上练习著正念、正智,一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修行上面了。
天魔波旬是欲界最高天他化自在天的一位天主,可说整个欲界都在他的掌握中,每当有人得以脱离欲界、投奔自由时,就代表他能掌握的人又少一位。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人民叛逃,波旬自然也是如此,喜欢考验能够脱离欲界的修行者,或鼓吹五欲的娱乐、或给僧团制造一些事件,希望人们乖乖地享受欲界,不要比他还强。
《杂阿含经》“魔相应”的内容为本卷第1084~1103经,记载和魔波旬有关的事件。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寿命甚促,转就后世,应勤习善法,修诸梵行。无有生而不死者,而世间人不勤方便专修善法、修贤修义。”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为诸声闻如是说法:‘人命甚促,乃至不修贤修义。’我今当往,为作娆乱①。”
时,魔波旬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常逼迫众生, 得人间长寿,
迷醉ⓒ放逸心, 亦不向死处。”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是恶魔来作恼乱。”即说偈言:
“常逼迫众生, 受生极短寿,
当勤修精进, 犹如救头然,
勿得须臾懈, 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恶魔, 速于此灭去。”
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 “王舍城”,巴利本作 Rājagaha。
ⓑ “波旬”,巴利本作 Pāpiman。
ⓒ “醉”,圣本作“酒”。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稣ⓐ息①,变易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行,厌离、不乐、解脱。”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为诸声闻说如是法:‘一切行无常、不恒,非稣[*]息,变易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厌离、不乐、解脱。’我当往彼,为作娆乱。”即化作年少,往诣佛所,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寿命日夜流, 无有穷尽时,
寿命当来去, 犹如车轮转。”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是恶魔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日夜常迁流, 寿亦随损减ⓑ,
人命渐消亡, 犹如小河水。
我知汝恶魔, 便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 “稣”,圣本作“苏”。*
ⓑ “减”,圣本作“灭”。
佛陀开示诸行无常,天魔波旬则抬杠表示寿命没有穷尽,就像轮回没有止尽,这是一种“常见”。佛陀的回答则将讨论拉回到现实上,表示人的寿命是持续减少的,类似“是日已过,命亦随减”的意思。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于后夜,洗足入室,敛身正坐①,专心系念。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夜起经行,于后夜时,洗足入室,正身端坐,系念禅思。我今当往,为作娆乱。”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我心于空中, 执长绳羂ⓐ②下,
正ⓑ欲缚沙门, 不令汝得脱。”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我说于世间, 五欲意第六,
于彼永已离, 一切苦已断。
我已离彼欲, 心意识亦然ⓒ,
波旬我知汝, 速于此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 “羂”,宋本作“衒”。
ⓑ “正”,大正藏原为“政”,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正”。
ⓒ “然”,大正藏原为“灭”,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然”。
① 敛身正坐:收敛身体而端正地坐着。
② 羂:捕捉鸟兽的网。读音同“倦”。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罗网”,相当的南传经文作“陷阱”。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右胁卧息①,系念明相②ⓑ,正念、正智,作起觉想③。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乃至作起觉想。我今当往,为作留难④。”即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何眠何故眠? 已灭何复眠?
空舍何以眠? 得出复何眠?”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爱网故染著, 无爱ⓒ谁持去⑤?
一切有余尽, 唯佛得安眠,
汝恶魔波旬, 于此何所说。”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 “迦兰陀”,巴利本作 Kalandaka。
ⓑ “相”,宋、元、明、圣四本作“想”。*
ⓒ “爱”,宋、元、明、圣四本作“受”。
① 右胁卧息:向右侧躺而休息。
② 系念明相:连续不断地念著光明的相。又译为“系念明想”、“系心在明”。
③ 作起觉想:作要醒起来的想法,不贪睡。相当的南传经文作“意念作起身想”。
④ 留难:阻留、刁难。
⑤ 爱网故染著,无爱谁持去:由于有贪爱如网而执著,没有贪爱就不会被牵着走。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爱网著诸有,遍覆一切处”,相当的南传经文作“该者没有欲缠、执著、渴爱,能引导到任何地方”。
本经中波旬要捣蛋,而表示佛陀既已证涅槃又何必休息?
纵使有禅定力的人不须要多少睡眠,佛陀不会故意显示他很神勇、不须睡觉,而是如同正常人般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行、住、坐、卧都正念正智,示现四众皆可实践的修行。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世尊于夜暗时,天小微雨,电光睒现①,出房经行。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夜暗微雨,电光时现,出房经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执大团石,两手调弄,到于佛前,碎成微ⓐ尘。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若耆阇崛山, 于我前令碎,
于佛等解脱, 不能动一毛。
假令四海内, 一切诸山地,
放逸之亲族, 令其碎成尘,
亦不能倾动, 如来一毛发。”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房,正身端坐,系念在前。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夜起经行,后夜入房,正身端坐,系念在前。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大龙,遶佛身七匝①,举头临佛顶上,身如大船,头如大帆,眼如铜𬬻②,舌如曳电③,出息入息若雷雹声。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犹如空舍宅, 牟尼心虚寂,
于中而旋ⓐ转, 佛身亦如是④。
无量凶恶龙, 蚊虻⑤蝇蚤等,
普集食其身, 不能动毛发。
破裂于虚空, 倾覆于大地,
一切众生类, 悉来作恐怖。
刀矛ⓑ枪利箭, 悉来害佛身,
如是诸暴害, 不能伤一毛。”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旋”,圣本作“游”。
ⓑ “矛”,圣本作“𨥨”。
① 匝:环绕一圈称为一匝。
② 𬬻:火炉,通“炉”。
③ 曳电:闪电。
④ 犹如空舍宅,牟尼心虚寂,于中而旋转,佛身亦如是:佛陀静默的心是空寂的,犹如空房子,佛陀的肉身则像在这空中旋转(的一点空间)。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我处于闲寂,系心正解脱,安禅修其身,如昔诸佛法”,相当的南传经文作“凡为了睡眠使用诸空屋,那位自我抑制的牟尼,舍弃后他应该在那里过生活(行),对像那种的他确实是适当的”。
⑤ 虻:昆虫纲双翅目虻科动物的通称,体形小的如家蝇,大的如熊蜂,有刺吸式口器,吸食牛等牲畜血液,有时也吸食人血。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毘婆罗山①七叶树林石室②中。
尔时,世尊夜起露地,或坐或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安身卧息,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毘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夜起露地若坐若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而坐,右胁卧息,足足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为因我故眠? 为是后边故?③
多有钱财宝, 何故守空闲?
独一无等侣, 而著于睡眠?”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不因汝故眠, 非为最后边④,
亦无多钱财, 唯集无忧宝。
哀愍⑤世间故, 右胁而卧息,
觉亦不疑惑, 眠亦不恐怖。
若昼若复夜, 无增亦无损,
为哀众生眠, 故无有损减。
正ⓑ复以百枪, 贯身常掘动,
犹得安隐眠, 已离内枪故⑥。”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王舍城”,巴利本作 Rājagaha。
ⓑ “正”,圣本作“政”。*
① 毘婆罗山:摩竭陀国首都王舍城周围的五座山之一,位于王舍城的东部,和耆阇崛山、广普山、白善山、仙人掘山环绕王舍城。又译为“毗诃罗山”、“鞞哆逻山”。
② 七叶树林石室:王舍城毗诃罗山上的一个石窟,因窟前的七叶树而得名。佛陀灭度后,迦叶尊者率领五百贤圣在此结集三藏。又译为“七叶树窟”、“七叶窟”、“七叶屋”。
③ 为因我故眠,为是后边故:你是因为自我而睡觉吗?还是因为已最后一世了而睡觉?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云何无事务,而作于睡眠?安寝不[寤-吾+告]寤,如似醉人眠”,相当的南传经文作“你以懒惰躺卧或者陶醉在诗中的吗?”
④ 最后边:苦的最后尽头,表示此生后就不再轮回。
⑤ 哀愍:悲悯。
⑥ 正复以百枪,贯身常掘动,犹得安隐眠,已离内枪故:纵使有一百支枪常贯穿挖掘身体,还是能安稳地睡眠,因为已离于内在的枪。按:“已离内枪故”可参考《中阿含经》卷六十第221经箭喻经当中拔毒箭的比喻。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譬如有毒箭,人射中其心,数数受苦痛,犹尚能得睡。我毒箭已拔,何故而不睡?”相当的南传经文作“即使刺箭已进入他们的胸中,心臓急速颤动地,这里即使那些被箭射到者也得到睡眠,已离刺箭的我{因此}[为何?]不应该睡?”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毘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
时,有尊者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①侧ⓑ黑石室ⓒ中,独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饶益,时受意解脱身作证②,数数退转;一、二、三、四、五、六反退,还复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寻③复退转。
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我独一静处思惟,不放逸行,精勤修习,以自饶益,时受意解脱身作证,而复数数退转;乃至六反,犹复退转。我今当以刀自杀,莫令第七退转。”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毘婆罗山侧七叶树林石窟中,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侧黑石室中,独一静处,专精思惟,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六反退转,而复还得。彼作是念:‘我已六反退,而复还得,莫令我第七退转,我宁以刀自杀,莫令第七退转。’若彼比丘以刀自杀者,莫令自杀,出我境界去,我今当往告彼大师。”
尔时,波旬执琉ⓓ璃柄琵琶,诣世尊所,鼓弦ⓔ说偈:
“大智大方便, 自在大神力,
得炽然④弟子, 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当制, 勿令其自杀,
何闻佛世尊, 正法律声闻,
学其所不得, 而取于命终。”
时,魔说此偈已,世尊说偈答言:
“波旬放逸种, 以自事故来,
坚固具足士, 常住妙禅定。
昼夜勤精进, 不顾于性命,
见三有可畏, 断除彼爱欲,
已摧伏魔军, 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忧恼,琵琶落于地,内怀忧戚已,即没而不现。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来,共至仙人山侧黑石室所,观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杀。”
尔时,世尊与众多比丘往至仙人山侧黑石室中,见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告诸比丘:“汝等见此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不?”
诸比丘白佛:“唯然,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见瞿低迦比丘周匝遶身黑暗烟起,充满四方不?”
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此是恶魔波旬于瞿低迦善男子身侧,周匝求其识神⑤,然比丘瞿低迦以不住心,执刀自杀。”
尔时,世尊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记。
尔时,波旬而说偈言:
“上下及诸方, 遍求彼识神,
都不见其处, 瞿低何所之?”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如是坚固士, 一切无所求,
拔恩ⓕ爱根本, 瞿低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瞿低迦”,巴利本作 Godhika。
ⓑ “仙人山侧”,巴利本作 Isigili-passa。
ⓒ “黑石室”,巴利本作 Kāḷasilā。
ⓓ “琉”,圣本作“瑠”。
ⓔ “弦”,大正藏原为“弦”,今依据宋、元、明、圣四本改作“弦”。
ⓕ “恩”,明本作“[恩-大+夕]”。
ⓖ “般涅槃”,巴利本作 Parinibbuta。
① 仙人山:即仙人掘山,王舍城五山之一。
② 时受意解脱身作证:一时亲自得到了依定力所得的暂时解脱(由定力而压住烦恼不起)。按:“意解脱身作证”是一种定境(犹如“八解脱”是指八种禅定),这样的定境会因生病等因素而退失。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得时解脱,自身作证”,相当的南传经文作“达到暂时的心解脱”。
③ 寻:不久;随即。
④ 炽然:猛烈燃烧的样子,在这里引申指明亮、明白的样子。
⑤ 识神:心识。
本经提到瞿低迦尊者从“意解脱身作证”的定境退转六次后,第七次为避免再次退转,而以刀自杀。
“意解脱身作证”是一种禅定,瞿低迦尊者退转的是定力。菩提比丘将此译为“他达到暂时性心的释放”,并引注释书解说这是“世间等至”,也就是禅定与色界定。生病可能造成这样的定力退失,但解脱智慧不会退失。
综合绝大多数经、律的看法,阿罗汉的解脱是不退的。那么瞿低迦尊者是在何时证得阿罗汉?古来即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北传的传统一般认为他是在临命终时或中阴阶段证般涅槃(“中般涅槃”),只有少数如《大毗婆沙论》认为有的阿罗汉可能短暂退转,但命终时必定再次证得阿罗汉,并举瞿低迦尊者为例。南传的注释书则认为瞿低迦尊者在以刀自杀时是凡夫,在临命终时证阿罗汉。
瞿低迦尊者以刀自杀的行为古来也有许多争议,毕竟佛教戒律禁止杀生,亦不许自杀。然而对于圣者而言,佛陀在证悟后曾考虑直接入涅槃,也有不少阿罗汉随缘入火光三昧自取灭度,足见圣者可以坐脱立亡、自在生死。不过这些是圣者程度的特例,凡夫东施效颦会有严重的恶果,就像本卷第1083经中说健壮的大象拔起莲藕冲一冲就可吃下去,但瘦弱的象没洗干净莲藕,和著泥土一起吃容易消化不良甚至病死。
就圣者的层次来说,瞿低迦尊者以刀自杀所代表的是不顾性命的精进修行,正如佛陀在本经偈中所说:“昼夜勤精进,不顾于性命”。人身是四大所造,对身体的过度使用自然会加速死亡,焚膏继晷的修行人、操劳过度的俗世人都是如此。瞿低迦尊者以刀自杀也可算是极端的精进,重点在于不顾性命的精进,而不在于挥刀自杀的表相。
就相关的经载而言,卷三十七第1024经记载阿湿波誓尊者在重病时无法像平日入四禅,而遗憾无法入定,佛陀教导他把心念放在觉知五阴无我、贪瞋痴永尽的解脱上,他就因为法喜而痊愈了。卷四十七第1265经、1266经另有两位比丘以刀自杀但证得阿罗汉的记载,重点不在于怎么死的,而在于是否能彻底解脱于五阴。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郁鞞罗ⓐ①聚落尼连禅ⓑ河②侧,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独入一空处, 禅思静思惟,
已舍国财宝, 于此复何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习近人?
既不习近人, 终竟ⓔ何所得?③”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已得大财利, 志足安寂灭,
摧伏诸魔军, 不着于色欲。
独一而禅思, 服食禅妙乐,
是故不与人, 周旋相习近。”
魔复说偈言:
“瞿昙若自知, 安隐涅槃道,
独善无为乐, 何为强化人?④”
佛复说偈答言:
“非魔所制处⑤, 来问度彼岸,
我则以正答, 令彼得涅槃,
时得不放逸, 不随魔自在。”
魔复说偈言:

“有石似凝膏, 飞乌ⓕ欲来食,
竟不得其味, 损觜⑥还归空,
我今亦如彼, 徒劳归天宫。”
魔说是已,内怀忧戚,心生变悔,低头伏地,以指画ⓖ地。
魔有三女,一名爱欲ⓗ,二名爱念ⓘ,三名爱乐ⓙ,来至波旬所,而说偈言:
“父今何愁戚, 士夫何足忧?
我以ⓚ爱欲绳, 缚彼如调象,
牵来至父前, 令随父自在。”
魔答女言:
“彼已离恩爱, 非欲所能招,
已出于魔境, 是故我忧愁。”
时,魔三女身放光焰,炽如云中电,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我今归世尊足下,给侍使令⑦。”
尔时,世尊都不顾视。
知如来离诸爱欲,心善解脱。如是第二、第三说。
时,三魔女自相谓言:“士夫有种种随形爱欲,今当各各变化,作百种童女色、作百种初嫁色、作百种未产色、作百种已产色、作百种中年色、作百种宿年色,作此种种形类,诣沙门瞿昙所,作是言:‘今悉归尊足下,供给使令。’”
作此议已,即作种种变化,如上所说,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归尊足下,供给使令。”
尔时,世尊都不顾念。
“如来法离诸爱欲。”如是再三说已。
时,三魔女自相谓言:“若未离欲士夫,见我等种种妙体,心则迷乱,欲气冲击,胸臆破裂,热血熏面。然今沙门瞿昙于我等所都不顾眄,如ⓛ其如来离欲解脱,得善解脱想。我等今日当复各各说偈而问。”复到佛前,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爱欲天女即说偈言:
“独一禅寂默, 舍俗钱财宝,
既舍于世利, 今复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习近人?
竟不习近人, 终竟何所得?”
佛说偈答言:
“已得大财利, 志足安寂灭,
摧伏诸魔军, 不着于色欲,
是故不与人, 周旋相习近。”
爱念天女复说偈言:
“多修何妙禅, 而度五欲流?
复以何方便, 度于第六海?
云何修妙禅, 于诸深广欲,
得度于彼岸, 不为爱所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身得止息乐, 心得善解脱,
无为无所作, 正念不倾动。
了知一切法, 不起诸乱觉,
爱恚睡眠覆, 斯等皆已离。
如是多修习, 得度于五欲,
亦于第六海, 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习禅, 于诸深广欲,
悉得度彼岸, 不为彼所持。”
时,爱乐天女复说偈言:
“已断除恩爱, 淳厚积集欲,
多生人净信, 得度于欲流ⓜ,
开发明智慧, 超逾死魔境。”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大方便广度, 入如来法律,
斯等皆已度, 慧者复何忧?”
时,三天女志愿不满,还诣其父魔波旬所。
时,魔波旬遥见女来,说偈弄⑧之:
“汝等三女子, 自夸说堪能,
咸放身光焰, 如电云中流。
至大精进所, 各现其容姿,
反为其所破, 如风飘其绵。
欲以爪破山, 齿啮破铁丸,
欲以发藕丝, 旋转于大山。
和合悉解脱, 而望乱其心,
若ⓝ能缚风足, 令月空中堕。
以手挠ⓞ大海, 气嘘ⓟ动雪山,
和合悉解脱, 亦可令倾动⑨。
于深巨海中, 而求安足地,
如来于一切, 和合悉解脱,
正觉大海中, 求倾动亦然。”
时ⓠ魔波旬弄三女已,即没不现。
ⓐ “郁鞞罗”,巴利本作 Uruvelā。
ⓑ “尼连禅”,巴利本作 Nerañjarā。
ⓒ “魔波旬”,巴利本作 Māra pāpiman。
ⓓ “往”,明本作“住”。
ⓔ “竟”,元本作“意”。
ⓕ “乌”,明本作“鸟”。
ⓖ “画”,宋本作“昼”。
ⓗ “爱欲”,巴利本作 Taṇhā。
ⓘ “爱念”,巴利本作 Arati。
ⓙ “爱乐”,巴利本作 Rāga。
ⓚ “以”,圣本作“已”。
ⓛ “如”,圣本作“知”。
ⓜ “流”,圣本作“海”。
ⓝ “若”,大正藏原为“著”,今依据高丽藏改作“若”。
ⓞ “挠”,大正藏原为“抒”,今依据宋本改作“挠”。
ⓟ “嘘”,大正藏原为“歔”,今依据元、明二本改作“嘘”。
ⓠ “时”,大正藏原为“如”,今依据高丽藏改作“时”。
① 郁鞞罗:摩揭提国的村名,佛陀曾苦行六年的地方,今日印度比哈尔邦的 Urel 村,义译为“苦行林”,又译为“郁毘逻”、“优楼频螺”。
② 尼连禅河:恒河支流。位于中印度摩竭提国伽耶城的东方,相当于今日印度比哈尔邦的帕尔古河。又译为“尼连然河”。
③ 若求聚落利,何不习近人?既不习近人,终竟何所得:如果你修行是为了在人群中获得名利,那为何不亲近人群?既然不亲近人群,那你修行到底是为了获得什么?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既能遗国荣,亦不悕名利,何不与诸人,而共为亲友?”相当的南传经文作“你在村落中曾做任何罪行吗?你为何不与人作友情?与任何人你的友情不生起?”
④ 独善无为乐,何为强化人:独善其身、自己享受无为的(无造作的、涅槃的)快乐就好了,何必强求教化他人?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既以得妙法,宜常戢在怀,诚应独了知,何以教众人?”相当的南传经文作“请你离开也请你就一个人走,你为何教诫其他人?”
⑤ 非魔所制处:不受魔所控制的地方,指为了解脱而来求法的人们,以和动机不纯正、为了抬杠而来提问的魔波旬作对比。相当的《别译杂阿含经》经文作“人不属魔者”,相当的南传经文作“他们问无死亡领域”。
⑥ 觜:“嘴”的异体字。
⑦ 给侍使令:听从使唤而侍奉。
⑧ 弄:嘲讽、取笑。
⑨ 以手挠大海,气嘘动雪山,和合悉解脱,亦可令倾动:如果用手能阻挠大海,吹气能移动雪山,那么已解脱于所有因缘和合事物的佛陀,也是能动摇的。按:这是指不可能动摇佛陀,有如手不可能阻挠大海、吹气不可能移动雪山。
本经记载了知名的佛陀成道时天魔波旬及三魔女依序试练佛陀的事件。
波旬试着怂恿佛陀,先是说“何不习近人?”劝佛陀别在清净处修行,要去和人群混在一起。佛陀不为所动,表示已得解脱之乐因此不需要和人群混在一起求娱乐。于是波旬再尝试相反的方向,表示“独善无为乐,何为强化人?”要佛陀不为众生说法。佛陀也不为所动,表示随缘说正确的答案,来人精进则自然解脱自在、出脱魔境。
也就是说佛陀既不染著于群众,也不会吝于随缘教化,让众生得解脱。波旬徒劳无功,只好低着头走了,接着由其三位女儿爱欲、爱念、爱乐试练佛陀。当然,佛陀也早看破了爱欲、爱念、爱乐,而不为所动。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树下,初成佛道。
天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门瞿昙在郁鞞罗住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佛道。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自变身,作百种净、不净色①,诣佛所。
佛遥见波旬百种净、不净色,作是念:“恶魔波旬作百种净、不净色,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长夜生死中, 作净不净色,
汝何为作此, 不度苦彼岸?
若诸身口意, 不作留难者,
魔所不能教, 不随魔自在②。
如是知恶魔, 于是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① 自变身,作百种净、不净色:自己变化身形,变出上百种清净或污秽的形象。相当的南传经文作“显示各种不同辉耀的容色:清净的与不清净的”。
② 若诸身口意,不作留难者,魔所不能教,不随魔自在:凡是身、口、意,不(贪爱、执著而)给自己造成障难的人们,魔不能诱导他们,他们不会顺从魔的控制。相当的南传经文作“凡以身与语,以及以意善防护者,他们不是随顺魔控制者,他们不是魔的随从”。
在天魔捣乱时,佛陀能够认出他,知道他的把戏虚妄不实,就可以说:“如是知恶魔,于是自灭去”,天魔就自然离开了。
在起烦恼时,持戒修四念住的人能够认出烦恼,知道烦恼的虚妄不实,接下来烦恼往往会减弱甚至自然消失。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正觉。
尔时,世尊独一静处,专心禅思,作如是念:“我今解脱苦行。善哉,我今善解脱苦行,先修正愿,今已果得无上菩提①。”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大修苦行处, 能令得清净,
而今反弃舍, 于此何所求?
欲于此求净, 净亦无由得。”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知诸修苦行, 皆与无义俱,
终不获其利, 如弓但ⓐ有声。
戒定闻慧道, 我已悉修习,
得第一清净, 其净无有上。”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但”,大正藏原为“弹”,今依据宋、元、明、圣四本改作“但”。
① 先修正愿,今已果得无上菩提:先前所发的成佛大愿,现在已得到成果,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相当的南传经文作“我确实到达了解脱的菩提”。
天魔讥讽佛陀不再进行日食一麻等逼迫自身的苦行,佛陀则表示修习戒定慧才能成就无上的清净,执著于外道苦行的表相并没有意义。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娑罗婆罗门聚落ⓐ。
尔时,世尊晨朝着衣持钵,入婆罗聚落乞食。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晨朝着衣持钵,入婆罗聚落乞食,我今当往,先入其舍,语诸信心婆罗门长者,令沙门瞿昙空钵而出。”
时,魔波旬随逐佛后,作是唱言:“沙门!沙门ⓑ!都不得食耶?”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汝亲ⓒ于如来, 获得无量罪,
汝谓呼如来, 受诸苦恼耶?”
时,魔波旬作是言:“瞿昙!更入聚落,当令得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正[*]使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如彼光音天①, 常以欣悦食。
正[*]使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常以欣悦食, 不依于有身②。”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娑罗婆罗门聚落”,巴利本作 Sālāya-brāhmanagāma。
ⓑ “沙门”,圣本作“瞿昙”。
ⓒ “亲”,大正藏原为“新”,今依据宋、元、明、圣四本改作“亲”。
① 光音天:色界二禅天的最高天。光音天人不用口语沟通,而以光互通心意,所以称为“光音”。光音天人以喜悦为食。
② 有身:由五阴构成的我。音译为萨迦耶。举例而言,执著于“五阴是我”的见解,则称为身见、有身见、萨迦耶见。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波罗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已ⓓ解脱人天绳索,汝等亦复解脱人天绳索。汝等当行人间,多所过度,多所饶益①,安乐人天,不须伴行,一一而去。我今亦往ⓔ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波罗㮈[*]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为诸声闻如是说法:‘我已解脱人天绳索,汝等亦能。汝等各别人间教化,乃至我亦当至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不脱作脱想, 谓呼已解脱,
为大缚所缚, 我今终不放。”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我已脱一切, 人天诸绳索,
已知汝波旬, 即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㮈”,宋、元、明三本作“柰”。*
ⓑ “波罗㮈”,巴利本作 Bārāṇasī。
ⓒ “鹿野苑”,巴利本作 Migadāya。
ⓓ “已”,明本作“以”。
ⓔ “往”,宋、元、明三本作“住”。
① 多所过度,多所饶益:多多度化、多多利益(众生)。
本经记载佛陀建议已解脱的尊者们在人间随缘教化时,不须要结伴同行,可以各自一一而去,这样能接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蒙受佛法的利益,也可见佛陀教化众生的慈悲。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①。
时,石主释氏聚落多人疫死。处处人民,若男若女,从四方来受持三归,其诸病人,若男若女,若大若小,皆因来者自称名字:“我某甲等,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举村举邑②,皆悉如是。
尔时,世尊勤为声闻说法。
时,诸信心归三宝者,斯则皆生人、天道中。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勤为四众说法。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何为勤说法, 教化诸人民?
相违不相违, 不免ⓑ于驱驰③,
已ⓒ有系缚故, 而为彼说法。”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汝夜叉当知: 众生群集生④,
诸有智慧者, 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 不能不教化,
哀愍诸众生, 法自应如是⑤。”
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而”,宋、元、明、圣四本无“而”字。
ⓑ “免”,圣本作“勉”。
ⓒ “已”,大正藏原为“以”,今依据宋、元、明、圣四本改作“已”。
① 石主释氏聚落:位于拘萨罗国的释迦族村落。“石主”为以石头砌成的围栏,为此释迦族村落的特征。
② 邑:城市。
③ 相违不相违,不免于驱驰:(人们听了法后)有的排斥、有的不排斥,难免造成劳心、费力。按:举例而言,听法的人排斥,则可能引起世俗说法者的瞋心,听法的人喜爱,则可能引起世俗说法者的贪心。相当的南传经文作“在顺从与排斥上执著”。
④ 众生群集生:众生共同生活着。相当的南传经文没有这几个字。
⑤ 法自应如是:本来就应该如此;自然就应该这样。又译为“法尔如是”。
波旬化作的少年质疑佛陀说法是否是因为有执著?佛陀当然不执著,而是哀愍众生所以说法,有智慧的人自然会哀愍众生。
不只波旬曾这么质疑,卷二十二第577经记载曾有天人也问佛陀为何要说法?佛陀回答:“一切众生类,悉共相缠缚,其有智慧者,孰能不愍伤?善逝哀愍故,常教授众生,哀愍众生者,是法之所应。”意义和本经偈诵相同。
许多人说法是为了获得认同,甚至是为了名闻利养,那么来人排斥说法就起瞋心、来人接纳说法就起贪心,而无法解脱。相较之下,佛弟子说法是为了解脱而自利利他,也可参照《中阿含经》卷八〈未曾有法品4〉第33经侍者经:“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初无是心:‘我受此法,为教语他。’诸贤!但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故。”
对于重病的人,佛陀教他们皈依三宝,因此“诸信心归三宝者,斯则皆生人、天道中”。
接引临终者皈依三宝,纵使对方还无法接受四圣谛等较深的法义,也能由信心而得益。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
尔时,世尊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颇有作王①,能得不杀,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独一禅思,作是念:‘颇有作王,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我今当往,为其说法。”化作年少,往住佛前,作是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可得作王,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善逝!今可作王,必得如意。”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而告魔言:“汝魔波旬,何故作是言:‘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魔白佛言:“我面从佛闻作是说:‘若四如意足②修习多修习已,欲令雪山ⓐ王③变为真金,即作不异④。’世尊今有四如意足,修习多修习,令雪山王变为真金,如意不异⑤。是故,我白世尊:‘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佛告波旬:“我都无心欲作国王,云何当作?我亦无心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何由而变?”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正[*]使有真金, 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 亦复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 金石同一观。”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雪山”,巴利本作 Himavanta。
ⓑ “者”,元本作“言”。
① 作王:担任统治者。
② 四如意足:基于四种因素产生禅定、成就神通:(1)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2)精进定断行成就如意足、(3)意定断行成就如意足、(4)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又译为“四神足”。
③ 雪山王:雪山这座巨大的山。“山王”指诸山中最高大的山,经中提到的“山王”有十座,以雪山王为首。
④ 即作不异:(雪山王)即可变作真金而没有差别。
⑤ 如意不异:如同意念所愿而没有差别。
由本经的问答可以推测:佛陀思考有无推行正法律的国王,是为了教化的思考,而不是为了自己要有权势而思考国王的作为。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事。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少壮婆罗门像,作大萦髻①ⓒ,著兽皮衣,手执曲杖,诣供养堂,于众多比丘前默然而住。须臾,语诸比丘言:“汝等年少出家,肤白发黑,年在盛时,应受五欲庄严自娱,如何违亲背族,悲ⓓ泣别离,信于非家,出家学道?何为舍现世乐,而求他世非时之乐?”
诸比丘语婆罗门:“我不舍现世乐求他世非时之乐,乃是舍非时乐就现世乐。”
波旬复问:“云何舍非时之ⓔ乐就现世乐?”
比丘答言:“如世尊说,他世乐少味多苦,少利多患;世尊说现世乐者,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能自通达,于此观察,缘自觉知②。婆罗门!是名现世乐。”
时,婆罗门三反、掉头、喑痖③,以杖筑④地,即没不现。
时,诸比丘即生恐怖,身毛皆竖,此是何等婆罗门像,来此作变?即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故。有一盛壮婆罗门,萦发大髻,来诣我所,作是言:‘汝等年少出家……’”如上广说,乃至三反、掉头、喑痖,以杖筑地,即没不现。“我等即生恐怖,身毛皆竖,是何婆罗门像,来作此变?”
佛告诸比丘:“此非婆罗门,是魔波旬来至汝所,欲作娆乱。”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凡生诸苦恼, 皆由于爱欲,
知[*]世皆剑刺, 何人乐于欲?
觉世间有余, 皆悉为剑刺,
是故𭶑⑤慧者, 当勤自调伏。
巨积真金聚, 犹如雪山王,
一切ⓕ受用者, 意犹不知足,
是故𭶑慧者, 当修平等观⑥。”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释氏”,巴利本作 Sakka。
ⓑ “石主”,巴利本作 Silāvatī。
ⓒ “髻”,大正藏原为“发”,今依据宋、元、明、圣四本改作“髻”。
ⓓ “悲”,大正藏原为“悉”,今依据前后文改作“悲”。
ⓔ 大正藏无“之”字,今依据宋、元、明三本补上。
ⓕ “切”,大正藏原为“人”,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切”。
① 萦髻:盘发为髻。“萦”,读音同“营”。
② 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能自通达,于此观察,缘自觉知:灭除如火烧般逼迫身心的烦恼,不须等待时令季节,能亲自正确地趣向(涅槃),就在这里当下看到,亲自能体证。
③ 三反、掉头、喑痖:皱眉、垂头丧气、说不出话来。“三反”为“三条皱纹”之义。相当的南传经文作“摇头、吐舌、额头上蹙出三条沟使不愉快的神情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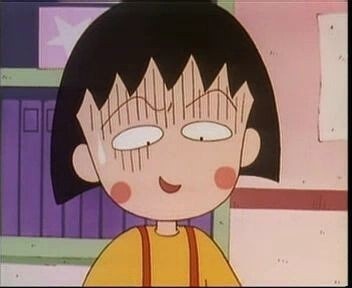
④ 筑:触、击。
⑤ 𭶑:同“黠”,聪明。读音同“狭”。
⑥ 当修平等观:应该要修习心中平等、不执著。
本卷记载了许多天魔波旬骚扰佛弟子的事件,而佛陀也教导弟子面对天魔波旬的解法,首先要看穿魔扰,像佛陀直接叫出波旬的名字后通常他就退下了,如同网络上的骇客被纠出本尊后通常就会收敛。纵使叫不出名字,知道是魔扰也能处理,例如卷四十五“比丘尼相应”记载很多比丘尼纵使不知道来者名号是天魔波旬,但知道是魔扰而不为所动。
最重要的是守护根门而于六境不系着,正念、正知五阴无我而不动摇。
- 第1100经:知是魔扰,正念念佛,觉魔为幻化。
- 第1102经:知五阴无我、无我所,而无所著。
- 第1103经:于六境不贪、不系着。
卷九第243至247经也解说超越六境即解脱魔系:“有眼识色可爱、可念、可乐、可著,比丘见已,知喜不赞叹、不乐着坚实,有眼识色不可爱、念、乐、著,比丘见已,不瞋恚、嫌薄。如是比丘不随魔,自在,乃至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卷一第21经则表示不为五阴动摇则解脱波旬:“若色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如是受、想、行、识动摇,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都和本卷相呼应。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
时,有尊者善觉①ⓐ,晨朝着衣持钵,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坛②,置右肩上,入林中,坐一树下,修昼ⓑ正受,作是念:“我得善利,于正法、律出家学道;我得善利,遭遇大师如来、等正觉;我得善利,得在梵行、持戒、备德、贤善真实众中。我今当得贤善命终,于当来世亦当贤善。”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有声闻弟子名曰善觉,着衣持钵……”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大身,盛壮多力,见者怖畏,谓其力能翻覆ⓓ发动大地,至善觉比丘所。
善觉比丘遥见大身勇盛壮士,即生恐怖。从坐起,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着衣持钵……”广说如上,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见有大身士夫,勇壮炽盛,力能动地,见生恐怖,心惊毛竖。”
佛告善觉:“此非大身士夫,是魔波旬欲作娆乱。汝且还去,依彼树下,修前三昧,动作彼魔,因斯脱苦③。”
时,尊者善觉即还本处,至于晨朝,着衣持钵,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食已,还精舍……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
时,魔波旬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住于释氏,有弟子名曰善觉……”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复化作大身,勇壮炽盛,力能发地,往住其前。
善觉比丘复遥见之。即说偈言:
“我正信非家, 而出家学道,
于佛法僧ⓔ宝, 正念系心住。
随汝变形色, 我心不倾动,
觉汝为幻化, 便可从此灭。”
时,魔波旬作是念:“是沙门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善觉”,巴利本作 Samiddhi。
ⓑ “昼”,元、明、圣三本作“尽”。
ⓒ “住”,大正藏原为“往”,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住”。
ⓓ 大正藏无“覆”字,今依据元、明二本补上。
ⓔ “法僧”,大正藏原为“无价”,圣本作“诸僧”,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法僧”。
① 善觉:比丘名,佛陀曾称赞他“得喜行德,无若干想”,《中阿含经》卷四十三〈根本分别品 2〉第165经记载佛陀为他说跋地罗帝偈(贤善偈):“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后略)”。又译为“三弥提”、“三弥离提”、“娑弥陀”。
② 尼师坛:坐时或卧时垫在身下,以保持衣服干净的长方形布。又译为坐具、敷具。
③ 动作彼魔,因斯脱苦:处理掉那件魔事,因此而解脱魔事之苦。
遇到魔扰时不要惊慌失措,正念系心于佛而不为所动,觉察到异象是魔所幻化,魔自知无趣,便会退去。
佛陀没有帮比丘赶走魔,而是让他自己练习如何应对。不只给他一条鱼,而是教他钓竿怎么用,让比丘真正地超越魔境。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波罗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声闻作师子吼,说言:‘已知,已知。’不知如来声闻于何等法已知、已知故作师子吼?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
时,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波罗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为诸声闻说法,乃至已知四圣谛。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何于大众中, 无畏师子吼,
谓呼无有敌ⓑ, 望调伏一切?①”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如来于一切, 甚深正法律,
方便师子吼, 于法无所畏。
若有智慧者, 何故自忧怖?”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 “瞿昙”,巴利本作 Gotama。
ⓑ “敌”,圣本作“歒”。
① 何于大众中,无畏师子吼,谓呼无有敌,望调伏一切:你为何在人群中无所畏惧地狮子吼?是想呼喊说自己无人能敌,想要打败一切对手吗?相当的南传经文作“你为何在群众中,如狮子般自信地吼?因为有你的对手,你认为是胜者吗?”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①中,与五百比丘众俱,而为说法,以五百钵置于中庭。
尔时,世尊为五百比丘说五受阴生灭之法。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与五百比丘俱,乃至说五受阴是生灭法。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大牛,往诣佛所,入彼五百钵间,诸比丘即驱,莫令坏钵。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非是牛,是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色受想行识, 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实灭ⓐ, 于彼无所著。
心无所着法, 超出色结缚ⓑ,
了达一切处, 不住魔境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灭”,大正藏原为“义”,今依据宋、元、明三本改作“灭”。
ⓑ “结缚”,圣本作“缚结”。
① 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王舍城中一处大众通行的空旷原野。
佛陀为比丘们开示“五受阴生灭之法”,即凡夫所执著的五阴有生即有灭,都是无常的。
这时,波旬为扰乱众人,化身为一头大牛,直奔比丘们摆放钵的地方。
比丘们看到钵即将被破坏,就坐不住了,急忙跑去驱赶大牛,一时之间场面混乱不堪,正中波旬下怀。
佛陀看破波旬的伎俩,提醒弟子们:“如果能知五阴非我、非我所有,不执著于五阴,便能超出其束缚,而不住于魔境。”
从实修的角度来看,佛弟子虽理解“五受阴生灭”的道理,但当名声、地位、身体或财产遭受损毁时,往往难以泰然处之。然而,若能在这样的处境中基于对佛法的净信来观察生灭,将逆境转为修观的机会,修行便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佛陀点破当下的情境是魔考,能让当事人转换视角,跳脱出负面的情境:犹如小朋友打电动,不会因为失败几次才成功通关一次而心灰意冷,反而会因为那一次的成功通关而愈挫愈勇。同理,修行人若在遇到状况时,能跳脱出情境的制约,以“正见”与“正志”面对世间的挑战,以正向的心态应对魔考,有助于在苦难的世间愈挫愈勇,持续修行。
如是我闻:
一时,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与六百比丘众俱,为诸比丘说六触入处集、六触集、六触灭。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为六百比丘说六触入处是集法、是灭法①,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壮士,大身勇盛,力能动地,来诣佛所。
彼诸比丘遥见壮士,身大勇盛,见生怖畏,身毛皆竖,共相谓言:“彼为何等,形状可畏?”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是恶魔,欲作娆乱。”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色声香味触, 及第六诸法,
爱念适可意②, 世间唯有此。
此是最恶贪, 能系着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圣弟子,
度于魔境界, 如日无云翳③。”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① 六触入处是集法、是灭法: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触物、意识法而影响身心,都是因缘生起的现象、因缘灭去的现象。例如由于有无明、贪爱等因缘,外境能让人心意动摇,而这些也都会灭去。“六触入处”指由“六触”进入身心的管道,常特指六触使人心意动摇、产生贪爱的过程、时空、或情境。六触是“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这里的“触”特指感官、外境、识,三者接触,是十二因缘之一。
② 爱念适可意:喜爱、思念、顺从、惦记。相当的南传经文作“这是可怕的世间诱惑物”。
③ 云翳:阴暗的云。